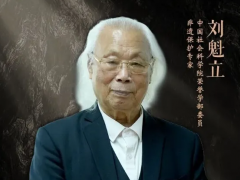方辉,1964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和考古学史研究,著有《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合著)、《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合著)、《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拼合历史:考古资料的阐释》等专著、译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议组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殷商学会副会长,美国《亚太考古》、奥地利《世界史前史杂志》编委会委员。
自16岁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起,方辉教授便与传统文化结下一生的缘分,尽管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那一代人最开始选择考古专业,还谈不上是因为多么高大上的理想和情怀,更多的是对能够走出书斋,去到野外实地调查发掘来研究第一手资料的向往,但正是因为这一小小的向往,冥冥之中选择了考古成为决定一生命运的节点,在之后数十年与青灯黄卷相伴的岁月里,在用双脚丈量历史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考古对自己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
魅力考古:永远给人一种期待
在大多数人眼里,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就是整日在田间荒野里与黄土废墟为伴,亦或是在各种垃圾堆和古坟里挖掘那些我们看起来只是岁月久远的普通器物碎片,考古就是一项远离现代文明且枯燥无聊的工作。然而在方辉教授的生动讲述下,考古工作不仅远非那样简单枯燥,而且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与乐趣。
“在田野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每次都抱有很多的期待,当你的发现和前期预判相吻合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开心。”方辉教授这样说道。当然,预判是源于深厚的学科功底和长久的积累。关于这种期待的乐趣,方辉教授特别讲述了一次新发现。在承担莱芜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任务的时候,他们在莱芜市牟汶河南岸的山顶上发现了一些石头构筑的防御工事,其结构和齐长城非常类似,于是提出假设,这些防御工事很可能就是鲁长城,然而历史文献中并没有鲁长城的建筑记载,所以引起争议,但在方辉教授看来,鲁长城的概念却是可以坐实的。“一是它的位置和齐长城南北向对,北岸就是齐长城,我们在南岸调查了30公里的防御工事,它们陆陆续续可以连接起来,虽然没有明确的有关鲁长城的记载,但是记载鲁国曾设置并废弃‘六关’,而关口往往就具有军事防御的职能,而且春秋时期几次重大的战役,像长勺之战,还有夹谷之会都发生在两长城之间,所以结合记载来看,鲁国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也有自己的前沿阵地,鲁长城的存在应该是合理的。”这些石构建筑的年代学证据,就是在若干个山头上采集到的春秋时期的一些陶片。“这说明当时人们不仅住在山下,还在山头上活动,这肯定是他们在当时利用了这种险要的自然环境来构筑自己的防御工事。”
当然,关于鲁长城的存在目前还只是个假说,要证明这一点,工作还会继续下去。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历史太过浩瀚,于文献当中记载的只是九牛一毛,而那些大量未被记载的史实需要考古人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去发现。“无论是调查发掘,还是案头的文献梳理,你总是有一个期盼,正是兴趣指导你不断向前探索,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这就是考古的魅力。其实不光是考古,探索未知本身就是让人愉快的事情。”方辉教授充满兴致地说道。
学科繁荣:一代考古人的幸运
虽然在方辉教授的讲述中,考古工作充满如此多的魅力和乐趣,但是事实上,由于考古材料往往带有很大随机性,可能很多考古工作者一生中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发掘名不见经传的遗址,而且由于材料性质的巨大差异性,导致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说到这,方辉教授感慨,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3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获得极大发展的30年,从本科教学、科研手段、服务社会的能力以及国际化建设可以说全方位得到发展,每念及此,方辉教授都感到有一种“赶上了”的幸运。
随着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从遗址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方式也比以前丰富的多,由于科技考古的介入,传统考古学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革命,在这方面我们晚了西方30多年时间,改革开放后睁开眼看世界发现我们落后了很多,所以这30多年是我们奋起直追的一个阶段。”方辉教授介绍,如今我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考古实验室,以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为例,有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陶瓷器分析、同位素分析和地学考古等,使得学科领域突然的扩张,考古学正变成一个非常开放的、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门学科,有人说这是“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不仅如此,从90年代开始,随着考古和文物对外开放政策的出台,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与西方同行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国际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传统与现代在考古领域的结合与延伸让历史展现出了更加丰厚的魅力。
经过30年的奋起直追,我国的学科建设已经能够紧随国际的水平和脚步,但在方辉教授看来,仅仅做到“跟得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想真正的“引领前沿”,吸纳国外的技术手段之外,必须要有自己在方法上的创新。“比如我们考古和材料学科的几个年轻老师在做的一个古代大豆植物的驯化,就是一个方法上的创新,这对于其他植物的驯化课题的研究可能有启发意义。”方辉教授说道。
遗产保护:人文学者的责任所在
在谈及自己考古多年的感悟及认识时,方辉教授将自我认识的提高过程梳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考古学本体的认识加深,第二个阶段是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开阔视野也更新了理念,第三则是思考学术研究怎样服务社会发展,使知识惠及民众,承担更多义务的阶段。说到这里,眼下较为严峻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处在非常急迫的位置,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各种大型的机械工程瞬间就可把地上地下的遗产全部毁坏掉,得以抢救发掘出来的遗产数量恐怕连10%都不到,我们面临着文化的危机。”谈及此,方教授眼睛里掠过一丝凝重。“比如中国古村落,乡村文化里包含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在的农村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消失,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以一种活态的形式给保存下来,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方辉教授认为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例如英国约克郡公共考古项目,约克郡历史悠久,在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在地下留下一个还原罗马时代生活场景的时间隧道,考古发掘出来的牛奶厂、马厩、铁匠铺等都得到保护和利用,走到那个地方可以闻到马厩的味道,可以听到叮当叮当铁匠铺的声音。再比如伦敦市博物馆,馆址就建在一座罗马城墙的旁边,从休息厅的玻璃看出去,城墙就在身边,它与展厅陈列的罗马文物互相关照,融为一体,而且这个博物馆本身也将古代文化遗迹和现代城市融为一体。西方的成功案例表明,在城市改造的同时使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存是完全可行的。
现在国家已经对文化遗产保护给予高度的重视,之前提出“乡村记忆”工程,要求以书面、影像或者有目的的保存一些标本的形式留住乡村记忆;实施“天网工程”保护大遗址,安装摄像头监控遗址,防止盗掘,在像曲阜、龙山镇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些遗址公园,能够使民众受到一些教益,等等。尽管这些保护工程正在推进,但方辉教授也有一些担忧。“如果拿一个模式,到各地去推广,也是很危险的,那会造成千馆一面,现在已经存在很多雷同性和同质性现象。在地域文化差异很大的县市,所展示的民俗展览却都差不多,到各地看到的旅游纪念品也几乎全一样,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应该根据遗产所在地的历史传统、自然环境设计出符合当地特色的场馆、创意产品。”另外,令人无比担忧的,是害怕当地政府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对经济价值的重视超过保护目的,过度开发文化遗产,把它做为一个可以发财的产业来看待,同样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针对以上两点,方教授希望能引起各地政府的足够重视。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许多多的文化遗产都可能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消失殆尽,或覆灭在现代文明的钢筋水泥之下,身为一名人文学者,方辉教授和同事们也时常感到一种忧虑和时间的紧迫感。在他看来,在时代赋予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艰巨任务面前,人文学者具有更加义不容辞的责任。“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在文化遗产建设及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遗产的价值要靠这些人文学者进行挖掘、界定;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在此基础上将遗产价值以最合适的方式进行保护和呈现,法学、公共管理则在法律法规和公共管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现阶段我们在各学科和专业上的力量整合还是比较薄弱的,这导致了文化遗产人才的不足。这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眼下总的方向是向好的方面发展。”方辉教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