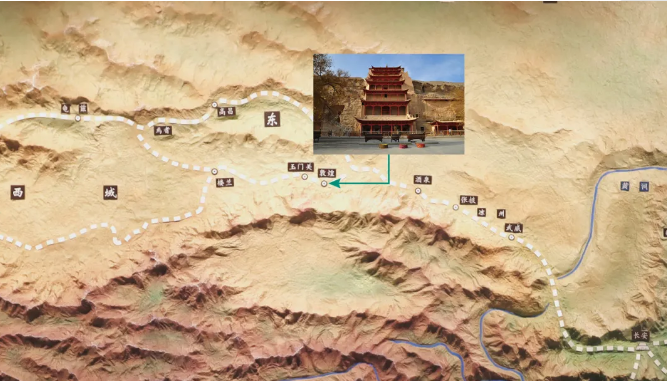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近七万号敦煌写本文献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交流交融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原本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写卷断裂成了一块块残卷或残片。通过类聚缀合,人们在分裂的残卷断片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破碎的文句、断裂的丝路文明被重新连接在了一起。
李学勤先生在谈到甲骨文残片的缀合时曾说:“甲骨文的缀合完全是创造性的,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渐展现出来,真是其乐无穷。”当看到原本骨肉分离”的敦煌写本碎片残卷经过拼接最终“团圆”的时候,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同样充盈在心间,让人激动不已。具体而言,敦煌残卷的缀合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恢复写卷原貌
据研究,敦煌文献源自道真搜集的古坏经文”,本多残卷残片。但在搜集入藏和藏经洞发现后的流散过程中,也有因种种原因而撕裂的,其可缀比例达25%以上。姜亮夫先生说:“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今天缀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原本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写卷重新拼合为一,让失散的骨肉团聚,这是敦煌残卷缀合的最大意义所在。
比如斯8167号,残片,存17残行,倒数第四行有“弟一世间医偈”字样,英藏敦煌文献》拟题“押座文”“第一世间医偈”。后经比对此残片与斯4571号维摩诘经讲经文》为同一抄手所书,而且就是从后者掉落下的一片,可以完全缀合,缀合后如图所示。其中斯8167号残片第3行“行行烈(列)座前”句后三字、16行“眼深岂易剜来减”句前三字均有若干残笔撕裂在斯4571号,缀合后则密合无间。所谓“弟一世间医偈”当校读作:弟一、世间医[王,善疗众病]。“偈”字后用冒号,领起其下韵文八句。与下文“弟二、世间父母忧其男女病。偈”云云格式正同,都是演绎上文所引用的《佛说维摩诘经》经文“以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众病”云云之意。斯8167号残片归位后,不但斯4571号《维摩诘经讲经文》第3片与29片之间原本脱落的大段文字得以基本复原,《英藏敦煌文献》斯8167号拟题的错误自然也就显而易见了。
确定残卷名称
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的比例相当大,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部分写卷虽有题名,但也每每存在题名歧异的情况。所以如何为写卷定名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也是“敦煌写本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之一”。一个完整的写本通常有自己的题目,但被割裂肢解成多个残片后,会造成原有篇题的缺失,所以有时局限在某一个残片上,未必能拟定准确的名称,而如能把相关的残片或其他异本汇聚缀合在一起,则有可能使篇题失而复得。
如刘复《敦煌掇琐》载伯2747、2648号“季布歌”,该二号均为残段,本身并没有篇题。所谓“季布歌”,乃刘氏据罗振玉《敦煌零拾》所载有相同内容的斯5440号“季布歌”(题目系罗氏拟定)比定的。《敦煌掇琐》紧接“季布歌”另载有伯3386号“季布骂阵词文”一卷,刘氏云“此与前二号字体不类,是另一人所写”。其实伯3386号即伯2747+2648号之后残缺的部分,三号字体完全相同,伯2648号末句“遂令武士”四字左部部分残画及“齐擒捉”三字在伯3386号,二者缀合后正好完整无缺。而伯3386号末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的尾题,则同一写本撕裂的伯2747、伯2648号自然也应改题“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残卷了。同样,斯5440号原本无题,也应当据伯3386号比定作“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或据另一异本伯3697号拟题作“捉季布传文”,而“季布歌”的题目则属无中生有,应予废弃。
确定残卷系统
由于译者或传承来源的不同,同一文献有时会有不同的译本或不同的传本,如《大般涅槃经》有北本、南本的不同,《金刚经》既有罗什译本,又有留支译本,《法华经》有《妙法莲华经》《正法华经》《添品妙法莲华经》的区别,《佛说佛名经》有二十卷本、十六卷本、十二卷本的区别,《燕子赋》有甲本、乙本的区别,等等;即便同是《妙法莲华经》,也还有七卷本、八卷本甚至十卷本的区别。这些不同的译本或传本,内容往往大同小异,仅就某一局部要判定其系统所属有时并不容易。而通过残卷的缀合,使孤立的残片拓展为相对完整的区块,则有助于我们对残卷的系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如日本滨田德海藏敦煌写卷的来源及真伪,向来为敦煌学界所关注。2016年9月25日,伍伦拍卖公司将其后人秘藏的36号写卷于北京举行拍卖,其中伍伦36号“《瑜伽师地论义疏》(孤本)”以人民币87.4万元成交。该本卷轴装,前后皆缺,存2纸66行,原卷无题,方广锠编著《滨田德海搜藏敦煌遗书》拟题同,该书序言称该卷“虽然首尾均残,却从来没有被历代大藏经所收,未为历代经录所著录,甚至是我们以前在敦煌遗书中也从来没有见过的海内孤本”。正由于这是一个“海内孤本”,这样的定名是否可靠,其实是不能让人放心的。后经发现,此本可以与北敦14734号缀合,二号内容于“谓于过去具有/诸见,于其未来具喜乐”句前后相接,中无缺字,可以完全缀合。后者卷轴装,首全后缺,存3纸97行,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一,弥勒菩萨说,无著菩萨造”,《国图》条记目录称该件与《大正藏》所载玄奘译本对照,“经文多所不同”。其实这二号既非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更不是只存“孤本”的《瑜伽师地论义疏》,而是吐蕃僧人法成译的《瑜伽师地论》残卷。法成译本是区别于玄奘译本的《瑜伽师地论》的另一个译本,仅敦煌文献中就保存了若干残卷。此二号与同属法成译的丹麦哥本哈根图书馆所藏MS12号、北敦14025号《瑜伽师地论》卷一经本字句基本相同,可以互证。
推断残卷时代
了解古书的成书和抄刻时代,才能确知它的史料价值或校勘价值。敦煌写本大都残缺不全,断头少尾,有纪年可确定具体年代者不多,所以为写本断代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
姜亮夫先生把敦煌写本的“定时”作为进入正式研究的前提,“能确切定时,则一切准备工作,可谓基本成熟了”。多年以前,我在谈到敦煌残卷的断代时,曾提出据内容断代、据书法断代、据字形断代、据纸质和形制断代四种方法,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其实还有另一种断代方法,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断代方法,即据缀合断代。当我们面对一个孤立的残卷甚至断片时,写卷能提供给我们的时代信息往往是有限的,但如果把相关的残卷系联起来,有关的信息就可成倍地增加,从而会给残卷的断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如北敦7183号、北敦2192号皆为佚本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卷五残卷,各存2纸、10纸,前后皆残,《国图》条记目录分别定作5—6世纪南北朝时期写本、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后来我们发现此二号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二号左右上下相接,衔接处断痕吻合,上下界栏对接无间,原本分属二号的“香”“佛”二字复合为一,可谓天衣无缝。此二号既可缀合为一,而《国图》条记目录断代不一,显有不妥。据二十卷本《佛名经》形成于隋代以后考之,结合书迹书风的总体观察,此组残卷或以断作唐代前期写本为近真。
明确残卷相关方
所谓相关方,是指跟写卷传播密切相关的人员,包括作者、抄者、校勘者、持诵者、收藏者等。一个完整的写卷,往往会有与相关方相关的或多或少的信息,而写卷的割裂,则会造成这些信息的丢失,缀合后则可使之失而复得。
比如俄敦102号、北敦6350号、北敦6432号都是《佛说佛名经》残卷,但各自前后残缺,又缺少完整的卷题,故前贤对其经本系统及具体卷数都存在歧义。后来我们发现,此三号可互相缀合,其后又可以与北敦6351号缀合,形成俄敦102号+北敦6350号+北敦6432号+北敦6351号的缀合系列。此四号内容前后相承,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近同,当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后一号尾题“佛名经卷第十三”,尾有题记“灵应写”,据此,可以判定此四号应皆为灵应抄写的《佛说佛名经》卷十三残卷。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有“灵应”题记且笔迹相同的《佛说佛名经》写卷还有北敦14456号、斯5341号。再查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灵应”其人见于伯3947号《吐蕃亥年八月寺卿蔡殷牒》、斯2614号背《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伯2250号背《沙州儭司儭状》、斯6005号《敦煌某社补充社约》、伯2250号背《沙州儭司儭状》等写卷,其身份分别为龙兴寺转经僧、乾元寺僧人、龙兴寺沙弥,生活在吐蕃时期819年前后、10世纪初到大约10世纪中叶、十世纪上半叶。前揭六号《佛说佛名经》写经的抄手“灵应”,极有可能属于这三个“灵应”之一。据此推断,其抄写时间大致可限定在9世纪初吐蕃时期至10世纪中叶归义军时期之间。
明确残卷属性
敦煌文献的主体是写本文献,具有实用的性质,其中既有精美的寺院写经,也有业已遗弃的兑废经卷;既有各级官府的文稿案卷,也有底层百姓的便条杂写;既有正式的法律文书,也有学郎的习字文样,各种文本混杂其间。人们在定名和撰写叙录时,往往需要判断残卷的具体属性,如官府公文、文样、兑废稿、杂写、习字等。另外,写卷的行款、用纸、字体等,也需要在叙录中加以交代。但敦煌文献残损严重,所能提供的卷面信息非常有限,加之霉污老化,导致卷面模糊,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并不容易。而通过与其他残卷的缀合,比较核验,就有可能发现彼此矛盾之处,并进而寻求确切的判断。
如北敦11814号、北敦9894号均为《佛说佛名经》残片,分别存10残行和4残行,《国图》条记目录分别定作7—8世纪唐楷书写本、5—6世纪南北朝时期隶书写本。后来我们发现此二号上下可以完全对接缀合,衔接处原本分属二片的“尒”“脩”“时”诸字皆得成完璧,接合凹凸处亦密合无间。由此可见,《国图》条记目录关于此二卷的抄写时间和书体的判断必然有误。通过分析写卷的用字特征(结体多呈正方形,中宫紧收)、笔法(已经具备典型的楷书写法),可知原卷应为6—7世纪楷书写本,个别笔画带有隶意,但绝非隶书。
判定残卷真伪
敦煌文献主要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文献。凡不属于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而从其他地方混入或后人仿冒假托的,皆可称之为伪卷。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文献中混入了不少非藏经洞文献甚至近人伪造的文献,所以写卷身份的鉴别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假如“问题”写卷能与可靠的敦煌写卷缀合,就可证明其可靠性,从而为其平反昭雪。
如1944年莫高窟中寺土地庙发现的一批古代写卷的来源,学术界曾有不同的声音,后来施萍婷发现这批文献有不少可与其他散藏的可靠的敦煌写卷缀合,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们确为藏经洞之物。又如2019年7月14日,伍伦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伍伦7号拍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以402.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一时引起轰动。该卷为著名敦煌学者兼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旧藏,卷前有著名书画家兼文物鉴定家启功题耑并钤印。原卷卷轴装,前缺尾全,存9纸181行,行间有非汉文夹注。伍伦官网上附载的方广锠叙录称:“从原件形态考察,确属藏经洞所出敦煌遗书……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有这么多重量级学者经眼鉴定,此卷的可靠性看来是不容怀疑的。然而,除了中、英、法、俄四大国家馆藏敦煌文献来历清楚、基本可靠外,其他公私机构和民间保存流传的敦煌遗书大多来历不明、真伪参半,购藏和研究都需特别谨慎。伍伦7号出现在拍卖行,被定为敦煌唐人写经,半卷佛经拍出400多万元的天价,然其真伪如何,人们不免还是有些疑虑。后经比对,此号前可与北大敦20号缀合,二号行款格式相仿,字迹书风似同,接缝处行间非汉文夹注字母残字可拼合为一,横向乌丝栏亦可对接,其为同一卷之撕裂可以无疑。伍伦7号既然可与北大敦20号完全缀合,不但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两个残卷的可靠性,提升了它们的文献和文物价值。